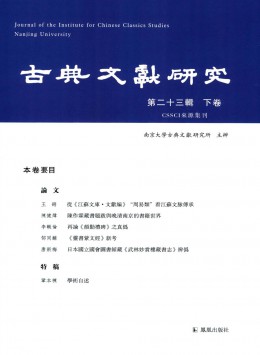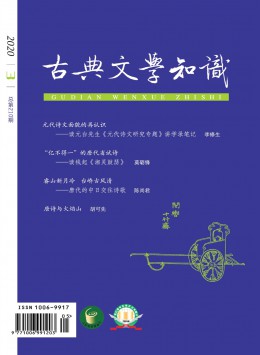古典戏剧女性形象研究

“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白虎通德论》)为了反衬男人自身的伟岸和无上权威,女性必须温柔、驯服。梁鸿少时孤贫,而孟光家境豪富,但孟光“常言道嫁的鸡儿则索一处飞,与梁鸿既为妻,也波相宜”,“重整顿布袄荆钗,收拾起娇红腻粉”,随夫无怨无悔地陋居草屋,布衣粗食。梁鸿虽然穷困,可在妻子眼里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天”,每顿饭妻子都是“高高的举案齐眉,服侍秀才”;在《威尼斯商人》中,当巴萨尼奥选中匣子成为鲍西娅的丈夫后,鲍西娅马上贬低自己是一个“不学无术、没有教养、缺少见识的女子”,她接着说:“幸亏她的年纪还不是顶大,来得及发愤学习;她的天资也不是顶笨,可以加以教导;尤其大幸的,她有一颗柔顺的心灵,愿意把它奉献给您,听从您的指导,把您当作她的主人、她的统治者和她的君王。我自己以及我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变成您的所有了;刚才我还拥有着这一座华丽的大厦,我的仆人都听从着我的指挥,我是支配我自己的女王,可是就在现在,这屋子、这些仆人和这一个我,都是属于您的了,我的夫君。”[2](四)奉献主观上无自我,具有忍辱负重的献身精神。《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在丈夫参加科举考试后,饥荒年,她独撑门户,典当首饰换回粮米侍奉年迈的公婆,自己吃糟糠,去义仓请粮遭勒索,走投无路欲寻短见时,还是想着无人尽孝的老人。公婆死后,她又卖发买席葬亲,罗裙包土筑坟。对待公婆,赵五娘尽心尽责;对待丈夫,她努力做到“贤”,包括容忍伤害自己情感的行为,蔡伯喈发迹娶相女牛小姐为妻,赵五娘没有表现丝毫不满。《香祖楼》中的曾氏为了给丈夫纳妾,不但请人去说媒,而且在女方“索要千金”的无理要求下,竟然从娘家借来银两;《救孝子贤母不认尸》中的李氏在丈夫死后,独自挑起家庭重担,勤俭持家、养蚕缫丝,辛辛苦苦抚育亲子杨兴祖和庶子杨谢祖。她因材施教,让两兄弟一学武一学文,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朝廷征兵时,为保护后妾遗孤杨谢祖,她坚决让亲生儿子奔赴“不死则伤”的战场;珀涅罗珀在漫长的20年中苦苦等待和消磨着自己的青春;《阿尔刻提斯》中斐赖城国王阿德墨托斯命中注定要短命而死,包括父母在内的亲人无一愿当替身,唯有妻子阿尔刻提斯自愿替死。
男性理想中的妻子除了美色、忠贞、顺从、奉献方面的要求之外,还关注于她是否能帮助丈夫逢凶化吉,逃避灾祸,获得权力、地位、身份等一切至高无上的荣耀。《杀狗记》中的杨氏可以说是这类女性的杰出代表。她在丈夫孙荣与奸险小人称兄道弟之时,想尽一切办法使冥顽不灵的丈夫走出歧途,在虎落平阳之前认清小人嘴脸,远小人,亲兄弟;《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因美丽的姿色被杨衙内看中,杨衙内设计陷害她的丈夫白士中。谭记儿勇敢地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仅惩治了恶人,还帮助丈夫渡过了危机;《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以过人的机敏,在法庭上欲擒先纵,唇枪舌剑,战胜了咄咄逼人的守财奴夏洛克,解救了一筹莫展的安东尼奥,制止了一场流血事件;《伪君子》中奥尔贡的续弦妻子艾米尔,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巧妙地帮助迷途丈夫幡然悔悟。在中西古典戏剧中,男性作家塑造了相当多的贤妻形象,她们身上承载着传统社会文化赋予女性美好品质的全部内涵,是男性对女性的期待与规范:貌美如花、忠贞不渝、温柔顺从、无私奉献、聪慧机智、宽容大度……对于男人们,要抚慰他们的心灵,包容他们的过错,担当他们的失责,要逆来顺受地承担,始终如一地忠贞,无私无我地奉献,尽心尽力地扮演好一个贤内助的角色,当然更要像谭记儿那样为丈夫清除一切麻烦。贤惠型女性身上所体现的贤德,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女性生命力的压抑、对女性自我精神的绝对控制,女性真实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已经被潜入了历史地表,作为人的女性的基本生存欲望和权利被抹杀和剥夺。为了实现妇女的美德,达到男性化标准,贤惠型女性以一切形式的牺牲(等待、忠贞、柔顺、臣服、甚至死亡)为代价放弃女性自我,从而得到男人的崇高评价。这类女性主观上无自我,具有忍辱负重的献身精神,以自己的枯寂生活和情感折磨为代价换来了在父权文化中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艺术源于生活,中西古典剧作家在刻画女性形象时之所以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正是因为中西古代的女性在生存空间上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固然也反映现实中女性的状况,但这种反映一经作家心灵的折射,就带上了作家的主观印记。男性作家在文本中依靠强大的男权话语建构了他们价值观认可的女性美德,这种美德是虚构的,是男性作家的“一厢情愿”,是男性作家试图将男权推向无可取代的极致地位的一种表现。同志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3]文学作品描绘的生活画面和客观存在的生活原貌不同,它是经过人类大脑加工再造的艺术形象,其中融进了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及其自身的理想、愿望和感情。
由于文化的差异,中西古典戏剧中这类女性形象同样有很多不同之处。
(一)家庭出身不同
在西方戏剧中这类女性形象多出身名门,而在中国戏剧中这类女性形象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在中剧中这类女性形象家境大都殷实富有,但并非达官显贵。因为有钱可以在文人困顿求仕过程中给予资助,帮助他们考取功名。《破窑记》中的刘月娥家里“有百万贯家缘”,刘员外虽不满意自己的贫穷女婿,并假装遣夫妻俩到破窑中,但却暗地里资助女婿上朝应举,没有刘员外的资助,恐怕也没有吕蒙正的发迹;《孟德耀举案齐眉》的梁鸿也是靠丈人的资助才平步青云。文人依靠妻子的资助考取功名,但又不要她们出身官宦,因为官宦容易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自身的价值难以实现。而西剧中这类女性不但家境富裕,同时多是贵族出身。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非常复杂,但中西接受主体不同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戏剧的受众群体基本上以中下层民众为主,他们偏好与他们身份、境遇相近的人物的家长里短、悲欢离合,因此作家塑造贤妻这类人物形象时必然考虑到这种审美要求,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这类群体的女性以博得观众的喜爱。西方的观众则以上流人士为主,而且喜欢看伟大人物的故事,因此,西剧中的很多女性大都出身高贵,王妃、公主、贵族之女等是作家、观众青睐的女性。
(二)贤妻的标准不同
中国古代的女性身受的清规戒律明显多于西方的女性,要想能成为中国男性眼中的贤妻良母,显然付出的和被要求的高于西方男性对此类女性的期待。除了美貌、顺从、忠贞这些男性眼中贤惠型女性不可缺少的条件外,中国古代贤惠型女性的标准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孝顺。因此,中国戏剧作品中刻画贤惠型女性形象时,基于“至善论”与“百善孝为先”的道德要求,几乎都把“孝顺”这一点作为塑造贤惠女性品质的重要尺度,赵五娘就是典型代表。西方社会也强调子女对父母应该孝顺、恭敬,但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最重要的首先是自己,其次才是他人。因此,西方贤惠女性的标准主要是对自己的丈夫忠贞,而对父母、公婆的态度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不成为衡量女性善恶的砝码。因此,在西方古典戏剧作品中,剧作家在表现女性的美德时,很少关注婆媳关系,也很少把孝顺这一点当作衡量女性的标准。
(三)经历的苦难不同
中国古典戏剧中的女性大都经历了来自身心的双重压力和苦难。刘月娥、孟德耀均来自殷实富裕之家,赵五娘初始也是小康之家,但为了显示她们的品德,作者无一例外地让她们从安逸走向贫穷,她们吃的是糟糠,穿的是布衣,住的是破窑。而在西方戏剧中的这类女主人公却很少面对这种生存困境。中华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强调自强不息的精神。《孟子告子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4]受此影响,大多戏剧家认为只有能够战胜艰难困苦、抵御外界诱惑的女性,才能苦尽甘来,凤冠霞帔,得到来自社会的最高奖赏——“贤惠”之殊荣。
(四)结局不同
西剧中这类女主人公大多以悲剧结束自己的一生,因为西方崇尚悲剧,主张把最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以取得最佳效果。《阿尔刻提斯》的女主人公为了实现妇女的美德,达到男性化标准,替代丈夫去死;苔斯德蒙娜则在阴谋中无辜死去。而中国则不同,善有善报的传统观念使作家必须给这些完美的形象一个完美的结局,因此在结局的安排上,总是不忘让这类女性夫贵妻荣、子孙发达,在道德奖惩中寓含强烈的理想旨向,即向传统的回归。
贤惠型女性的确包蕴了妇女很多优秀的品格:吃苦耐劳,勇于献身。然而这类形象是以牺牲自己的情感,付出一生为代价的,她们丧失了女人独立选择生活的权利,她们的一生是为丈夫而活,她们的人生价值是依赖男人得以实现的。我们可以这样说:被男性礼赞的贤妻只是男性中心意识的反映,是女性独立人格遭受钳制和扼杀的体现,贤妻是一种理念,并不是真实的生活,她们是男性中心意识里最完美的妇人,但不是一个真实的女人。理想化的贤惠型女性实质上是男性意识的一厢情愿,也恰恰表明作者没能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她们仍旧是尘世凡人,除了具有明显的人格缺陷外,她们和男性一样在生活中挣扎求存,被压迫,而不是那样生来完美、纤尘不染。中西古典剧作家对贤惠型女性形象的理想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传统男权对女性的统治支配心理,理想化的贤惠型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本文作者:刘云霞、邢满 单位: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 上一篇:农民思想文化的建构范文
- 下一篇:小议传统文化对管理职能的作用范文